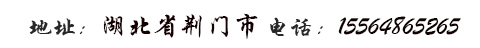初中花生作文闲坐凝视,文字可亲,永不凋零
|
. 花生作文、中考特训营、小初高 寒假招生 叶才生的课程目录 寒假 花生作文、小初高语数英物等 春季招生 叶才生领衔团队:中考全科特训营 寒假 中山书童 花生作文 在陌生而熟悉的惊艳风景里,遇见文学;在朴素而有温度的文字里,能复活我们已经沉睡的无边想象与超凡精神。文学的力量是渺小而飘逸的,关乎心灵的自我援助,关乎人生的美学生活。 推而广之,在文学的玫瑰时光里,心灵相遇,享受优雅汉语之美,这是极其美妙的成长记忆。 花生作文与读写,正是在诗经的两岸跋涉。从创意出发,通往高地与远方。 今天,刊发初中部学员的作品,与君分享。 摆,渡,跨过巨浪 初一 张毅峰 夏,闷。 夕阳仅有的那一滴血红,照在了那已然生锈的桌角。 我坐起身,那块犹如笼罩光明的黑板中,一抚粉笔刷印——心。 心,烦。 夏日那难得的一缕微风——起了。我抬起头,数学老师已在讲台上,整理着手头上的琐事。我,选择了枕在那只舒适的手臂中。 “好,宣布一件事。”数学老师那双清澈的眼睛从我身上流过,就像——在回避我。“我们多增加一个数学课代表,就……就小杰吧!” 我猛地抬起了头,眼神中充满了震惊,更多的是质疑。这,是为什么?我质问我自己,不解地看着老师。 他,数学才80多分啊,凭什么不给我这10分的学霸一个机会? “这……是随机选的吗?”嘴角情不自禁地冒出了一句。“你说什么?我选谁当我的课代表是我的事。我都想向班主任来提议把你的班长撤掉了,少说两句话不行?长大出去,呵,是会被炒掉的!真的是。” 老师双手撑着讲台,面无表情的脸上,那双浑浊的眼里,若隐若现地倒映出我难堪的身影。仅仅讲了不到一分钟的话,却那么长、那么久,以至于至今,那段话才时常在我耳边响起。我低下头。空洞。寂寞。 夏日那风,止了。 我从书包里掏出了口罩,眼神却模糊。我把它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难过。委屈。 空,已暗得无可捉摸。 强忍着,强忍着,别流下眼泪。多丢人啊,安静——别再说话便行了。 我看着屏幕上亮着的字迹,再也没有说话,只是动动手、写写字。 “好,你来说一下为什么a等于b,而a分之c却不一定等于b分之c?”老师期待地看着我。微微扬起的眉毛下,眼神明朗地闪着光。 “因、因为c会等于0。”我无力地回答。 “好,非常好!”老师笑了,那是愧疚的笑,轻抚着内心的波浪。“掌声呢?”一阵震耳欲聋的鼓掌响了起来…… 夏日那风,起了。 老师的职业不免受到质疑,可老师却总会一次又一次鼓励我们前行。深深地,爱着学生。 摆着,渡过了知识的海洋;穿过重重巨浪;跨过茫茫跌倒的瞬间。最终,你,带领我到达了成功的彼岸…… 夏夜的风,吹皱了黄昏。 一个少年,踏上了归途茫茫的夜路。 影子半天的爱 初一 樊卓熙 残留。残喘。 烈日,点燃了无名老者的苍发。老者纷纷逃离,慌不择路。天边,也只剩下那一抹酡红。 脚印镌刻在石头路上,一阵阵狂风从身旁呼啸而过,参差不齐的房子也都紧紧挨在一起。人们成群结队地走着,欢言笑语。 我也不孤独,我有影子。 影子是不会说话的,但我们用肢体交流,整齐地踏过一条条马路留下走过的痕迹,为什么只有一条痕迹呢? 隐隐约约我看到那栋房子了,脚下的漆黑,似乎也很高兴,不断地变长,那一抹鲜红也被突如其来的快乐刷去了一半。 忽然天边传来怒吼声,身披黑甲的马与士兵正一路驱赶光明,冰凉刺骨的汗水如万根尖锐的银针,直勾勾砸向地面。疼了,漆黑的淤青冒了出来。 我飞快地向屋檐下跑去,用手遮住额头,闭上眼,双脚来回摆动,身上的衬衣时断时续地变黑了。影子害怕雨,悄悄地躲起来了,只剩我一人狂奔。原本应该出现的明月也被他们挡住了。 终于来了,屋檐下。我气喘吁吁地坐着,身上并没有过多的打湿。一盏盏路灯各自亮了起来,都有一束光,也只有一束光。影子那漆黑的身影也钻了出来,被路灯拉长的他依偎在身边。我望着这场对大地的洗淋,不由得叹了声气。影子也想安慰我,却不知怎样让我听到他的心意,只能用手抱着,头靠着我,我的心里莫名多了一种熟悉的温暖。 雨,停了。 清亮的月镶在天上,洒下光辉。在月光和灯光的帮助下,我蹒跚的步履撑着我缓慢地向那栋房子摸去。踩过坑坑洼洼,小小水花也在空中飞舞,影子也凑上热闹,与他们共舞。 一场盛大的舞会,正热闹着。 滋啦,原本空洞的孔里嵌入一把闪着银光的钥匙,变得充实。推开大门,里面两个焦急而久候的身影向我冲来,紧紧抱着我,熟悉的味道和温度席卷而来,把我淹没。几滴晶莹从他们眼眶滑落,砸在了我的面庞。也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回过头,凝望。那黑色的影,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是一位患有抑郁症的人。当然,是别人这么说我的。 我想握住你的手 初一 康楒琂 夜,她缓缓睁开眼睛。 那双漆黑慵懒的眸子就是暗下来的天,泛着星星点点的光。 晚风吹拂,我身穿黑色的连衣裙,裙角随风翩跹。眼神空洞地看着那一口沉重的木棺材,甚至忘了哭泣,只是呆呆地立着,一动不动。 几个月前还看见您和善的笑,看见您手提着刚买的菜对我说声好,还不忘给我塞几个我儿时最爱的小吃。慈祥的背影我还依稀记得。 不忘的是儿时的老屋,长满青苔的石板,狭窄的小巷,落地无声的雪花;最想忘记的是来往的车辆,悲痛的亲人,黑色的棺材,您死时的模样。丧礼举办的时间似乎很长,不知有多久,只是浑浑噩噩走几个场,却觉有几个世纪之长。待结束之后,才猛然被冷风一吹,清醒些许。 午夜,入梦。 我好像又看见了您,看见您带着和善的微笑向我走来。我忍着泪奔跑过去,在您面前定定地站了许久。您问我,发生了什么让我这样委屈;亲切地呼我为小哭包,我破涕为笑。您拉起我的小手,向前走。我问您,我们要去哪,您低头用苍老的眼睛看着我,说,我们回家。我同小孩和一般乖巧地点点头,信服地任由您牵着我往前走,走着,看到前方的路很长,好像没有尽头。不知为何,微微吊着的心好像突然有了种莫名的安心感。 沿着前方的路一直走,环顾四周才发现沿途的美景:一汪波光粼粼的清泉,一片成林的树木,一棵不知名的野花野草,一直翩跹飞舞的蝴蝶。 脚止不住地向蝴蝶追去,挣脱掉您的手,如稚嫩孩童般不知无趣地追赶着蝴蝶,直至走远才发现您早已不见。只剩那一田向日葵开得正灿烂,一个小女孩正无助地掉眼泪,因为她弄丢了她至亲的人。 猛然惊醒,才觉方才不过一场梦。我,无奈只得苦笑。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想握住您的手,让您知道,手的温度来自我的心底。 夜,缓缓睁开眼。尽头,微光渐强。 爱,原来一直都在初二 李展琪 爱,不曾远离。成长路上,与爱相伴,便处处是沁人芬芳。——题记那年盛夏,栀子花依旧如期开放。 即将迎来小学毕业,本该高兴的我却发了愁: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主持毕业典礼的名额。我本该把握机会、展现自己,可我从小就不善言辞、胆小怯懦,一紧张就吞吞吐吐的,怎么能够主持毕业典礼呢? 正当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时,母亲迎面走了过来,不容置疑地说:“我已经和老师答应下来了,你总不会这点本事都没有吧?”母亲说完便转身离开。万一我没主持好,把毕业典礼搞砸了呢?为什么母亲从来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我呢?是否因为母亲对我的爱越来越少,才开始这么顽固呢?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母亲刮目相看。 每天放学,我便留在教室里,一遍遍背着枯燥的台词。可我不是忘了动作,就是忘了台词。我懊恼着,坐在角落的母亲却一声不吭,始终没安慰过我,只是皱了皱眉说:“我会等你到熟练为止,否则别想回家!”我只好愤愤地拿起已被揉皱的稿子,继续对着镜子练习。还未吃饭的我饥肠辘辘正想松懈下来,又看见母亲正注视着我的严厉目光,只好硬着头皮,不敢停下。 比赛终于如期而至,当我即将上台时,坐在台下的妈妈依然注视着我,但这目光少了一份平时怒目圆睁的严厉,多了一份鼓励的慈爱。我朦胧感觉到:其实,母亲也是关心我的吗? 是的,母亲一定是爱我的! 我紧张地走上了台,掌心里渗出了微微的汗珠。我的双腿有些发抖,忘记了如何开口。气氛忽然一片沉寂,我的手心也几乎拿不住话筒了。这时,我迎面对上母亲柔和的目光,心慢慢地放松了下来。母亲脸上不同往日的鼓励的微笑,给我的心注入一股坚定的力量。我鼓足勇气,自信地拿紧话筒,面带微笑,台词在我口中滔滔不绝地涌现。我的眼前浮现出母亲陪我练习的情景,是那双严厉的注视着我的眼睛,让我有了前进的动力。 母亲的注视,并不是冷漠,更不是无情,而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爱,陪伴着我坚持到最后;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殷切希冀,支撑着我告别懦弱,走向坚强与勇敢,让我在成长的路上,永不退缩…… 爱,原来一直都在,不曾离开。那属于母爱的沁人清香,一直沉淀在心底,盛开在平凡,芬芳在生活的琐碎中…… 母爱严肃,却无处不在,陪伴我的一生,使我成长! ——后记 晚风吹拂 初二 李伟豪 繁华声声,遁入空门。 夕阳拉着晚霞在西天一路狂奔。我撒开双腿,也追着它们,进了一座小山村。 灰色的青砖,锈色的红瓦,蛛网状碎裂的石板。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在拐角处等着。 狂风带着傍晚的些许宁静,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过来,仿佛想踏塌这座疲惫的小村庄。 “外婆!”我紧张地望着这一幕,如离弦之箭般冲过去,撞入她的怀抱,紧紧不放手。 “慢点儿,慢点儿,外婆在这,外婆在这,不怕啊。”她缓慢且轻柔地抚着我的背,抚平我心中的不安与彷徨。 我知道,就算大风让整个世界倾倒,她也会给我怀抱。 “累了吧?进去坐,外婆给你弄好吃的。”她牵起我的手,一步一步走进斑驳的木门,走到温暖的小屋里。 我坐在几经摇晃、似乎随时都要塌裂的藤椅上,看着外婆在昏暗灯光下,在厨房里若隐若现的忙碌身影。她的身影似乎有些虚幻。 抬手想抓住外婆虚幻的身影,想牢牢固住,却发现外婆已端着两盘香气萦绕的美味出来。“来吃吧。”她把菜摆好在饭桌上,向我招招手。 刚想起身,却发现四肢犹如被无形的铁链锁住了,动弹不得。用力一挣,却浑身一空,发现自己所处之处变了,落在了门前的布满尘埃的石板上。外婆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眼眸与皱纹一般深邃,望向远方的长野。 晚风又过来了,吹起她鬓边的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疤。外婆转过头看向我。浑浊的眼珠,一笑生花。她忽然起身,往远处走去。 暮色遮住她蹒跚的脚步,走走停停像幅画。 风拉着我往反方向走,我大声喊:“外婆,下次回来再看您!”声音仿佛穿过灰色。她回头笑了笑。 老树根盘踞在门边。 石板上幽悠回荡着的,是再等的恍然若梦。 奶奶与花 初二 邱媛 花低下头,俯身扎进孤独的夜。 奶奶很孤独。爷爷很早就走了,墓地躺在那片花海深处。奶奶后来也没有嫁人,还是住在原来那个破木房。她时不时会拿出爷爷的相片,凝视片刻便红着眼,落了几滴泪。奶奶的背不好,弯下去的时候划出很大的弧度,但她固执地不要拐杖。她爱养花,后院一大片花都是她养的,虽然都是些野花,没有牡丹那样名贵。奶奶也很守旧,永远穿着几件早已被水洗去原色的花衬衣。 那天。奶奶把我叫过去,因她要给花浇水。 今天,她显得异常快乐。酒窝挂在她的嘴角,她笑得像后院的那一片野花。我调侃说:“奶奶,这些不知名的小花有什么好看?您真该多养些名贵的花。”奶奶不说话,倔强地瞥了我一眼:“姑娘嘿,你愿意给奶奶拍几张照片吗?”我点点头。她转身走进屋里,打开一个陈旧的盒子,拿出一条长裙,是淡蓝色的布满白色的野花的图案。“好看吧,姑娘!”“真好看!”奶奶笑得像小女孩。她换上那条裙子,也招呼我帮她梳头。她把相机拿给我,而她靠着一棵树,手里捧着鲜花,尽管背还是弯的。咔嚓一声,便定格了。照片被洗出来,奶奶捧着它。久久凝视着。 她回到自己的屋子,也不再笑了。她找出一张相片,上面是年轻的她和年轻的爷爷在后院的样子。以前的奶奶靠着爷爷,现在的奶奶靠着大树。奶奶手上捧着鲜花,依旧。以前的奶奶亭亭玉立,现在奶奶的背被生活压弯了,似乎得了一种什么病。以前的奶奶害羞地笑着,现在的奶奶坦然地笑着。 以前,爷爷笑得明朗。 现在,爷爷在天堂看奶奶笑。 奶奶孤独地坐在躺椅上,晃啊晃。眼睛望向窗外的野花以及那棵树,不眨一下,逼着那滴眼泪回流。她眼里布满了遗憾。野花孤独地看着她,她也孤独地看着野花。她爱这些野花像爱爷爷。 花看不下去了,最后也把她带走了。在她生命的最后,只有仪器声伴着她,还有床头的一朵野花。她的手轻微地一个飘忽,扎进黑暗,不再抬起来。她孤独地走了。 奶奶很孤独,野花成了她的简写。 奶奶很孤独,奶奶很爱寂寞而燃烧的花。 秋之凄 初三 刘星宇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径幽鸟愈静,林衰秋更凄。 漫步小径,静赏其景。眼前的炽红,不知是枫还是一团团的熊熊巨火。枫那旺盛的生机令人惊愕。不过,也只有枫能违背天地之意愿,对抗季节之磨砺,在万物衰去之时,绽放出艳丽的生命之花。三个月的漫长沉默,终换得一朝的烈火燎原,枫可谓是植物界的普罗米修斯,将奥林匹斯的天火高高擎起,矗立于林梢间,想接过太阳的职责,照耀人间,而自己甘愿承受萧瑟秋风的折磨。他会和太阳神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凄寒、黑暗作出最动人心魄的搏斗。聚起一股枫之火终究不是永恒的炽焰,最终也只能付之一笑,灰飞烟灭。飘荡、零乱,落叶在疑惑,在犹豫自己的归宿。它们既然已有过轰轰烈烈的过往,那是否会拥有不平不平凡的归处。但大多数或伴万千如丝般的愁绪化为尘土,随萧瑟之秋风变得乌有虚乌,或与这黯淡殆尽的夕日,悲壮地坠入粼粼似镜般的清潭,回归安宁寂静的海之国。 此刻,一团“小火苗”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我的手心上,支离破碎的身体,温润如玉,细腻如脂,蕴含着秋泉之清凉,枫叶之幽香。 一步一景。风萧萧,树巍巍。黄叶无奈漫天飞。前叶飘,后叶随,可叹母树脚难追。银杏的凋零飘散极易引发诗人对时光的感慨。清晨的她仪态万千,与蓬勃的朝阳相互问好,大方地展示着自己的娇媚。可傍晚未至,她就似疲倦的孩童,意味着秋姑娘的肩头,甜蜜地睡去了。在此之前,回眸一笑百媚生,仔细地叮嘱最后一缕暮色:“晚安,明年别忘了叫我起床。”但谁曾注意到他流下了一滴金灿灿的“眼泪”。或许她一睡不醒,永远远地被世界遗忘。 你若叫来艺术家游园,他必会兴奋地宣布:溪水中有两件无与伦比的画作,一副应名《暮色》,另一副应为《最后的告别》。 风枝惊暗鹊,露草覆寒蛰。孤寂无声中,只有喜鹊在跳跃,落叶在飘舞。喜鹊那黑白相间的燕尾服上,还隐隐约约透出几分紫来,栖在树上时,尖尖的尾翼总是一刻不停地晃动。它们凝望着太阳,斜歪着脑袋,沉思着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将去何处?”。有时喜鹊似乎下定了决心,翅膀轻轻一拍,小脚微微一蹬,小巧玲珑的身子便消失在那片火烧云中,如来时般无声无息,似乎只是这小园里的匆匆美好过客。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黄昏时分使心中的凄冷又增了几分。夕阳突然射出万道金针,在一片眩目的光芒中,跃入了水中,只留下一片金灿灿的云。 我只能坐在红、黄、绿的斑驳中,慢慢地品尝,看着水雾、夕阳、时光从手中流逝。原来,这就是凄秋,一段无法挽留的金色回忆,落寞却不颓废,衰败而不死寂。 这次,选择细听蛙鸣 初三 郑兴宇 城市生活急而空虚,偶然乘兴,奔去乡郊,沉淀那急躁的心。 亭亭挺立,荷花放慢了我的脚步。夏风吹不弯它的腰,暗香轻拂,鼻腔一池清香。湖中正静,一声“呱”鸣撕裂静谧,搅动了我的心,惊现了湖中央一圈涟漪。 震,彻。蛙鸣俞渐繁密,好似每株荷花后都藏着一两只青蛙。一阵阵“呱呱”声,寂寞地环抱着夜中的湖。暗暗的回声从远处潜伏而来,附和着蛙鸣,满池清脆的响声,飘渺空灵,好似来自那星空。蛙鸣荡过芦苇,飘向远方,朝那亘古的地平线扩散,惊得晚霞悄然溜去,只留下半弧黑暗。夜在湖上睡去,可寂静却被驱散,无影无踪。 青蛙喊得更欢了。 湖中,一支乐队莅临。没有粉丝狂热的捧场,没有灯光炫丽的照耀,没有金光闪闪的乐器。只有夜。是的,无边的夜,默默地陪伴着青蛙乐团。简陋的荷叶,冷清的池塘,蛙鸣声不减,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肺腑的朴素之声,每一个停歇都是下一秒的蓄力。青蛙,不张扬的自己的嗓音,只为在这冷凄的夜中,增添少许生机。我渐渐愣住了,青蛙不顾一切,只为了奏响那淡淡的乐曲,为的是什么?夜,凄冷,它们却依然站在自己的舞台上,没有观众,仍旧诵那夜的赞歌。心弦似乎轻轻颤了一下,我对眼前这群蛙肃然起敬。 远处荡来一条舟,船夫头望星空,脚踏舟边,一手叉着腰,另一手攥着渔网。舟无声地划进荷花群中,警觉的乐队“扑哧”一声钻进水中,合唱戛然而止。是寂,是暗。既而又紧挨着夜,缓缓睡去。船夫见蛙蹦鱼惊,似是无奈,撑杆便走。舟在湖面上涂上一道破折号,继而消失在远处。城里的池塘,只有一片青葱的芦苇,几只火烈鸟雕像,一汪清潭,蛙鸣却无影无踪。而这里,蛙鸣响彻天际,清风十里,沉淀内心。 见此,我的心愈发清凉。往日那杯浑浊的水已愈发清澈,我正要转身离开—— “呱,呱——呱,呱——” 空灵的蛙鸣又再次回荡在夜空中。蛙鸣声愈发响彻,夜都为之震动。这是乡郊的演唱会,一场场平平凡凡,没有丝毫张扬的演唱会!蛙鸣虽响,却沉静了我不平凡的心,洗净了我的双耳,洗礼了我的灵魂。这时多么朴素的一支乐队!与城里那些高光喧哗的乐队相比,青蛙乐队更使我拥抱了大自然,这才是生命,这才称得上音乐。 时间不早,我已细听蛙鸣,乃转身离去。 身前,茫茫黑夜;身后,一池赞歌。 花开花落的瞬间 初三 谢杰韬 阳春三月,丁香花悄然开放。 还不到晚上八点,这时候丁香花花香浓烈,空气和树木仿佛被花香灌醉了。风放慢脚步,停止呼吸,静静地在一旁倾听花的歌唱。我站在窗边,喝着花香浸泡过的茶,无聊地看着窗外。 一声尖锐的爆鸣声,划破了云层,撕碎了弥漫在空气中的花香,把我从闲情逸致中拉了出来。几个小孩站在槐树旁,偷偷摸摸地玩弄手中的鞭炮。正值疫情期间,他们没有戴口罩,很显然是趁家长不注意,一路小跑、两步三回头地溜出来的。路灯照映下,他们斜长的影子变化出各种形状,像夜黑风高时山林里的精灵围着火炉跳舞一样。带头的那个男孩大声地说道:“我想这里应该没有人了,他们也找不到我们。”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小心翼翼地抽出一粒炮,用力往地上一摔,炸了。 爆炸迸发出来的爆鸣声,一次次惊醒树上歇息的鸟。火星四射,在黑暗中绽放出一朵朵光辉的花朵,转瞬即逝。孩子们的欢笑和尖叫声,也随着爆炸声跌宕起伏,空气中夹杂着一丝过年的喜庆。 十月份,中国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人们从居家生活中解放出来。 太阳躲起来,黄昏的阴影在丁香花丛中伸展开去。丁香花被秋季的凉风打在地上,零落不堪。残余无力的香气中,和着青草与泥土的清新。两位老人从槐树旁走过,眼睛里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其中一位摘下口罩,对着槐树深呼吸了一口,对着另一个人说:“我想这里应该没有人了,你也来感受一下久违的大自然的气息吧。”于是他们伫立在槐树前,看着树上古朴的枝干,轻轻地抚摸那干裂、条理分明的树干,像对待亲人一般深情地望着它,嘴里小声却振振有词地说道:“槐树跟咱们共产党一样,厚实……” 一阵风吹过,树上两片叶子翩翩落下,在空中飞舞旋转。梅花的香气从远处一里一里地传来。 他和他的力量 初三 麦淇森 病房是白色寂静的世界。 她捧着一盆含苞待放的花,走进死一般的寂静。她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看了一眼她手中的花,干涩的唇部动了一下,欲语无言。 又一片沉默。 在得重病前,他的父亲是一位花农,常常在家种花花草草,对四季花情有独钟。 在孩童时代,他就告诫她说,四季花虽不如玫瑰花那样绚丽动人,也不像牡丹花那样婀娜多姿,但它实在、能吃苦,能在恶劣条件下生存,花龄又长。做人也要像它一样,普普通通,、平平淡淡,却又坚韧耐劳。她满口答应,在他面前时而蹦跳,时而撒娇,朴素的服饰和机灵的头脑让她成了一株能跑能道的四季花。 前几天,她回城里找工作,结果接到了邻居的电话,她又火速赶了回来,医院。她其它的行李都没带来,就带了父亲送给她的一株四季花。 空旷的病房里,只能听到钟走的声响。 医生看了看他的脉,低声对她说:“他活下来的几率很渺茫,因为他要动一场大手术,很少人能挺过来。”她低着头,擦了擦眼泪,呜咽着说:“做吧。”“这是手术单,明早九点动手术,请你签字。”她提起笔,刷刷地写了几行字,连写的什么也不清楚。 那一晚,她紧紧握着他的手,彻夜不眠。皎洁的月光洒下,大地将窗台上那盆四季花照得雪亮。好几天没浇水的花已略显枯黄,几片破叶落在盆托上,犹如飞碟起舞。那一个雪白的花苞已经向下垂落,失去了昔日嫩粉的光泽。 几片乌云带走了月光。他在隆隆的雷声中被推进手术室,它在隆隆的雷声中苏醒;一滴麻醉药水缓缓流入他的体内,一滴雨水缓缓落进干燥的花盆。血从手术刀上落下,滴入托盆中;雨从叶尖滑落,打湿了落满破叶的土壤。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他在梦中感到五脏挪移;四小时、五小时、六小时,它在水的洗礼中完全苏醒。 手术室灯亮了,天晴了,她泪水朦胧的双眼睁开了。 他的呼吸恢复了,它的枝茎挺起来了;他的心跳正常了,它的枝叶长出来了;他的伤口日益见好,它的花苞日益变大;他的双眼睁开了,它的花苞绽开了。 他看了一眼她和它,笑了。 生命之花将永不凋零。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danhuaa.com/mdhjz/6700.html
- 上一篇文章: 光荣榜全苏州仅8人,2位是学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