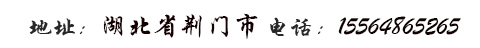第期文学园地清明专号崔淑红散
|
文学园地 清明专号崔淑红散文《常追忆永相思》 作者简介:崔淑红,河南洛阳人,本科学历。洛阳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洛阳女作家学会秘书长、洛宁县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期刊、报纸、杂志,网络平台。 常追忆永相思作者:崔淑红又将逢清明,路边的牡丹已娇颜初绽,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清冷中,想起那个对外婆的承诺,我要在牡丹盛开时带她来洛阳看牡丹。如今,她再也不可能来看牡丹花了,永远错过,抱憾终生..... 一常常会在一个人午睡的时候,听到一声轻轻的咳嗽,温暖熟悉,那是外婆所特有的咳嗽声。她有时候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有时候会站在我卧室的门口,喊着我:“乖娃,吃饭了!”就算我已是三十大几的中年人时,她依然会叫我乖娃。 睁开眼,只有白惨惨的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窗照进来,屋子里是一片无休止的寂静,没有外婆,没有人叫我乖娃,我只是梦见了她。 其实外婆从没有在我的这个家里住过,在我买了新房,有了宽大的三居室之后,我一直想要在春天的时候,接她来洛阳看牡丹,却始终不能成行。记得我们第一次来洛阳看牡丹,是八十年代初期牡丹花会时,那时我四五岁,是外公外婆爸爸一起带我来看的,那次在龙门石窟还差点把我弄丢了,外婆一直絮叨多次,说那次假如找不到我,把我丢了,该怎么办啊,她是没法活下去了!之后外公去世,她就再也没有来过洛阳。她说过很多次,啥时候能再去看一次洛阳牡丹就好了,我知道她一直思念外公,想念我们一起去洛阳看牡丹的时候。可是多少年了,她大多数住在我们村里的小姨家,别说带她出去玩,能回老家看看也是少之又少,那个时候,家里没有车,来一次洛阳要辗转倒车近一天才能到洛阳,我虽然心里一直记着,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我在洛阳有了新房之后,她却身体不好了,大部分住在县城母亲那里,我回去看她,说:“外婆,我有新房子了,今年春天一定带你去看牡丹”。她无力地看着我:“憨娃,我还是想去看,但不知道能不能去得了”。 那年冬天她住在几百里之外的二姨家,到了第二年春天洛阳牡丹花开的时候,身体依然不好,我一直想着去哪里借一个轮椅推着她看牡丹,却因一天天的忙碌而错过了牡丹花期。后来安慰自己,牡丹年年都会花开,下一年一定找个轮椅推着她去看牡丹。夏天的时候,她的身体更加不好,从二姨家回来,医院,但我还是没往坏处想,总觉得来日方长。星期天我回县城看她,陪她说话,她一直都是安静的,就算身体里长着距大的肿瘤,也从没有说过一句疼一句不舒服,她的一生始终都是安静的,温顺的。我说给她按摩身体让她舒服舒服,触摸到的却是令人惊心的瘦骨嶙峋,心里异常难过,她说:“乖娃,我想回家,你送我回去吧”!我说:“外婆,好的啊,但我明天要回洛阳上班了,我下个星期回来,送你回老家好不好”,她高兴的笑了:“中,下个星期送我回家”。 夜半时分,尖啸刺耳的手机铃声,让我惊的差点从床上掉下来,电话那端母亲泣不成声,我的脑子里有瞬间的空白,无法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一刻来的这么突然,这么让人无法承受。 那天,我们送外婆回家,初秋的阳光依然炽烈,可回乡的路上,却已有大片黄色的叶子在飘飞,风推涌着叶子茫然而毫无秩序的到处乱窜,白茫茫的天空,真的到了凋零的季节了吗?握向她的手,触摸到的是蚀心的冰凉,我不敢看她半睁着的眼睛,掠过她灰白的头发,看着天空,看着倒退的树木,看着记忆中再熟悉不过却很久没有走过的回乡的路,没有眼泪,只有彻心彻骨的疼痛。 荒芜的院子,野草疯了似的长了满院,我低声对外婆说:“外婆,我们到家了,你看,这是我们的家”,我不允许随行的医生拔掉她的氧气,我说外婆的眼睛明明是睁着的,医生无奈地摇摇头一声叹息。我看着外婆,我想听到她叫着我乖娃,可我再也听不到。明明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说话,外婆说她想回家,她想让我她送回去,我温柔地按摩着她的身体,在那惊心的瘦骨嶙峋中,我说,下个星期天,我一定送她回家,可我没想到一句话竞成了永别。 那些难熬的,为外婆守灵的日日夜夜,我一直坐在她的身边,半步都不舍得离开,时而昏睡,时而清醒,耳边时时刻刻充斥着悲痛欲绝的哭声,脑子里一片混沌。半梦半醒间,我看到外公笑着向我走来,我高高地坐在他的脖子上,在田野间,在山路上,在彩霞满天的黄昏里。小时候我们全家经常去外公上班的小镇上小住,几十路的山路,我只能走一小半,余下的路,都要靠外公来背,我会坐在他的脖子上,也会趴在他的背上,我惧怕黄昏,惧怕黑夜,在夜幕来临前,我会闭上眼睛,一会问问:“外婆,我们到了吗?外婆,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很多时候时候我会睡着了,醒来已经在外公的宿舍里,真喜欢那时候昏黄的电灯泡,那么温暖那么亲切。那时候,小镇上馋人的猪头肉,金灿灿的桔子,甜甜的甘蔗,红艳艳的大苹果,焦黄的火烧馍馍永远都塞在我的书包里,外婆和外公把我宠溺成了令镇上小孩羡慕不已的孩子。 二小时候,我喜欢的不是有父母亲的家,父亲工作在外,母亲整日劳作,那个时候小小年纪不仅要干活还要照顾妹妹,不到十岁的我,常常把小妹抱在胯骨上,从左边移到右边,再从右边移到左边,实在累得抱不动了,就把她放在桐树上一个悬挂着的竹篓里,慢慢摇,可她大概觉得竹篓里躺着不舒服,动不动就嚎啕大哭,没办法,只好把她抱起来重新挎在腰上,站在大门口,眼巴巴看着母亲回来的路,看不到母亲,就和妹妹一起哭。而在有外公外婆有大姨小姨的家,我却受尽宠爱。初夏时分,小山村里房子边上无边无际的槐花林,满沟沟坡坡的槐花似一场洁白的梦漫天飞舞,提着小篮子和小伙伴们满沟满坡的奔跑采花拔草。山下的芦苇地芦花随风疾疾低荡,河滩一汪汪清泉,无际的池塘,都是我们戏乐的天堂。 可是,外公怎么就不在了呢?那个骄阳似火的夏天,外公不在了,阳光炙烤着大地,梅园的梅子成熟了,似火一样映红了整个村子,我却再也不也能趴在外公厚实的背上撒娇,泪水奔涌的那样彻底,哭声撕心裂肺却再也唤不醒外公。 悲伤的日子过了许多,我依然喜欢住在那个小山村里。那些沟沟壑壑山山岭岭依旧是我们奔跑嘻戏的乐园,只是我渐渐长大,我随外婆姨姨们去田地里点瓜种豆、割草放牛,我仍然是那个她们时时疼爱的孩子。每次回我自己的家,大姨或小姨必有一个一起陪我回去,外婆和另一个姨则要送我们一程。那条山路上,有一个叫五里坡的地方长有一棵古老而高大的柿子树,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在那里,每次相送,也都是到那棵柿子树终止,到那里已经能看到山下我家的村子,外婆千叮咛万嘱咐才让我们离开。那曲曲弯弯、绵绵长长的山路,不论我走多远,回头都能看见高高柿树下两个小黑点,那是外婆在殷殷遥望...... 后来父亲母亲都工作在外公工作过的小镇,小姨在镇里一个村子里教书,大姨出嫁去了远方,外婆也经常在镇上小住,我们全家又快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很少再回到外婆家的小山村里,可我没有一天不思念那个地方,那些沟沟壑壑、山山岭岭,那一草一木,那高大的老柿子树,那满天飞舞的芦花,那满山满坡疯跑的我...... 在我长大了之后,慢慢知道外婆苦难的前半生。我知道了,为什么别人是一个曾外祖母,而我是三个,我一直很骄傲地对小伙伴说,我可是有三个曾外婆的,我过年可以得到三份压岁钱,而你们是一份,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眼神,让我得意极了,可我不知道,外婆遭受了多少苦难。 在外婆刚出生时,她的亲生父亲便被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不到二十岁的母亲几年后改嫁,是叔父婶娘收养了她。在她几岁还没有记忆时,原本富足的家庭,一夜之间被划成地主成份,她没有享受过大小姐的待遇,却被生活打入地狱。叔父忍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在一个黑夜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那苦难的岁月,死去的人得以解脱,活着的人却更加苦难。别说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婶娘自己的孩子也整日被饿的哇哇大苦,地主家庭,大人除了下地干活,还要被斗的死去活来,吃树皮,吃观音土,大冬天没有衣服穿,我无法去想象那种苦难的生活。而外婆还是活下来了,在善良婶娘的照顾下,如山间那贫贱的蒿蒿草,一岁一枯,春风吹又生,一年年长大。 长大,嫁人,有了女儿,就是我的母亲。生活似乎有了明媚的希望。 三一天无意见听到一个熟悉的阿姨对我说:“你外婆她老人家身体怎么样,她真是一可怜人啊,你妈两三岁的时候,你外公要娶别的女人进家门,就把你外婆和你妈赶出了家,当时我和你妈是邻居,她们两个没地去,就住在我家!你曾外祖母,不舍得你,不舍得你外婆,但是也没办法”。我当时就惊呆了,心里许多模糊的疑团终于被揭开,为什么小的时候父亲母亲要我去那个陌生的老人家走亲戚,那个所谓的爷爷婆婆,居然是负心赶外婆和母亲走的人。回家之后,问起母亲这件事,她叹了口气说:“过去的事了,别提了,怎么说他也是你亲的外爷,现在年龄也大了,再大的仇恨也放下了!” 我明白了我的三个曾外家母,一个是外婆的亲生母亲,一个是她的婶娘,一个是她第一个婆婆。 我一直以为最亲的外公,那个最疼爱我的外公,其实只是母亲的继父,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就算在他去世之后,我依然是那么想他,想念他宽厚的脊背,想他坚硬的胡茬子,想他在我不高兴时就挠我的小脚心逗我格格笑。那个亲生的外公,与我才是真正的没关系,那只是一个再也无法让人仇恨风烛残年的老人而已。 后来,外婆带着母亲和外公组成了新的家庭,外公是个军人,经历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的战争,一生刚正不阿,和外婆伉俪情深,却英年早逝。 外婆在那个小山村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十年。起初外公依然在部队上行军打仗,外婆一个人在家辛苦养育几个孩子,几十亩田地,不在坡上就在沟里,公婆早逝,没有人帮衬,其中的艰辛无法想象。我母亲从小就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吃尽了生活的苦,但她们的心里不苦,那才是真正的家!后来,外公从部队转回到地方,一家人才团聚在一起,外公说除了他一人在县里工作,吃公家粮,其余的家人都要在家种地,不能出去参加工作。外公除了在县里上班,抽空就回家种田,替外婆分担繁重的农活,对待我的母亲疼爱之极,和亲生的孩子没有任何分别。后来,外公又转到镇公社当领导,离家更近了,也有了更多机会回村里干农活,帮外婆减轻负担。 外婆四十多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其实只是普通的子宫肌瘤导致身体出血不止,医院查不出问题,用一个破旧的拖拉机拉到洛阳,医院,依然没有人知道外婆到底生了什么病。我父亲和外公觉得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看着躺在拖拉机上旧棉被里瘦弱不堪的外婆,决定拉她回家。无法想象当时外公心里有多痛,好容易打完仗,转回到地方工作,有了几个孩子,一切都是那么好,外婆却得了这样不明不白的病,且将不久于人世。 在外公和我父亲绝望地拉着外婆准备从洛阳回家时,在街头遇到了一个自家亲戚,那阿婆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她了解情况之后说:“说什么也不能把人拉回去,洛阳治不了咱去郑州,郑州治不了咱去北京,没去咋就知道治不了”。就这样,外公和父亲把外婆拉到了郑州,辗转找到一位洛宁老乡,当医院的医生,一场手术下来,总共花了二十七块钱,让外婆活了下来。多年以后,父亲总是无数次回忆起那场往事,他说,要不是当年遇到你那个阿婆,你外婆早就不在了,还有那个洛宁老乡,二十七块,是二十七块救了你外婆的命。 一切不幸似乎都已过去,母亲姊妹几个渐渐长大,日子越来越好。我小时候久住外婆家,在记忆里没有见过外公外婆吵过一次架,甚至一句嘴都没有拌过,外公永远都是笑呵呵的,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 可是,后来外公得了重病,他离去前一段时间,就一直躺在在病床上,一日日消瘦,我看见他深深陷下去的眼窝,并不知道这一切预示着什么,直到他离去,外婆伤心欲绝。记得那时小小的我,一个人靠在房子的土墙上哭,终于知道,外公永远离开了我,再也不能回来。记得那时在外婆家里有一个黑色木衣箱,里面压着外公的一枚枚军功章,军装、军帽。外婆经常会拿出来,一遍遍给我说起一些关于外公的往事,虽然年代久远,我已记不得她说过的事,可她坐在床铺上一遍遍喃喃自语抚摸外公遗物的表情,却刻划在我的脑海里,从未忘记。 一次一位老人到我们办公室办事,无意间说起我们居然是老乡,再说下去居然和外公是战友。 他说,你居然是老贺的外孙女呀,太意外了。对于你的外公我是太熟悉了。有一年,日本鬼子打仗打到我们这里,你外公正好回乡,没有来得及撤退,被几个鬼子围住房子,当时,屋子里就你外公和你曾外祖母两个人,是你曾祖母递手榴弹,帮你外公打退了鬼子,能活下来,真是不容易啊!闺女,见了你外婆,一定代我向她问好啊! 外婆的一生永远是柔软的,温顺的,瘦弱的,也是坚强的,她永远都是微笑的,不管生活有多么苦难。我总觉得她就是原野上的蒿蒿草,无闻柔软坚韧,她要哭也是会背过身去,我说外婆你怎么哭了,她说没有啊,灰眯眼睛里了,说着就会笑起来。在外婆过了七十岁之后,她依然不舍得离开那个没有多少人家的小山村,她一个人守着几亩薄田,麦子玉米瓜豆一茬茬种,顾不过来就叫小姨和姨父去帮忙,收完自家的,又背上竹筐去拾别人家地里遗留的。麦穗一个个捡回,在院子里摊开晾晒,用棒槌一点点去敲,用簸箕扬净,晒干收袋,她常常会骄傲地说:“我今年又拾了两袋麦子呢”。农闲了她就会烙一摞香脆脆的干饼,背上几个南瓜红薯,走近十里的山路,到小姨家,然后又坐客车到县城我母亲那儿,乐呵呵地拿出她的干饼给我们吃,遇到我在母亲那儿小住,她每天都在我还没有起床时,就把湿毛巾和饭菜拿到我的床前,叫着我:“乖娃,吃饭,被窝里暖和,吃了再睡一会”,这个习惯从我小时候一直延续到她生病不能起床后,那被宠溺的感受,想起来就忍不住流泪。我和母亲都会抱怨她不会享福,住县城多好,非要一个人在村里,让人不放心,她总是笑笑,住不了几天又要回去。其实那时母亲兄弟姊妹几个都过得不错,舅舅已是一个行政单位的主要领导,她完全可以跟着子女过清闲的好日子,可她就不舍得那个小山村。 外公走后,外婆的眼泪大多缘于小舅。小舅自从外公走后,就喜欢上了流浪,动不动就消失几年不见,把两个孩子和小舅妈留在家里,那时候信息不发达,如果一个人消失了,你便无从寻他。外婆一次次背过身去哭,逢从外地回来的村人就打听你们见我家小儿没,并一再交待人家,帮着留意小舅的消息,千恩万谢。小舅每次被寻回,过不了多久就会重新消失。为此无助的外婆迷上了求神问卦,听到有人算卦算的好,不管多远就要想方设法去算上一卦,看小舅在那个方向,那个位置,离家多远,我觉得可气又可笑,忍不住狠狠怼外婆:“整天去算,他都不想你,你想他干啥?”外婆讪讪笑了,觉得对不起我似的,说不想了,不想了。我记不清小舅到底离家出走过多少次,不知道外婆到底流了多少眼泪,对小舅的恨意一直到外婆不在。有一次母亲对说,想办法打听打听你小舅在哪,也不知道你外婆还能不能见上他。我恨意难平,说:“不打听,打听他干啥,一生对外婆没有尽过一天孝,娃子媳妇也不管,要他干啥”。母亲除了一声声叹息,就是去劝解外婆。直到外婆去世,也没能见上小舅,我心里是的的确确恨的。本来外婆的几个孩子都是孝顺的,日子过的也好,外婆可以顺心顺意地安享晚年,因为小舅让她伤心操劳了后半生。外婆去世的第二年小舅回来了,我见到他时,他有病刚做过手术不久,背明显驼了下去,已是快六十岁的老人,心里的恨就突然消失了,外婆你心里一直牵挂的小儿子回来了。我父亲有病住院期间,医院相陪,送去吃的用的,宽慰母亲,我知道了血浓于水就是如此吧,不管他做过什么,最终他都只能是我们的亲人。外公不在了三十多年,我知道他一定是一个人太孤单了,他想让外婆去陪着他。那一天,天空细雨纷飞,我们泪如雨下,沿着山路缓缓前行,我又看到了我们曾经劳作过的田野,看到了那些曾经的夕阳满天,那些牛儿哞哞叫的黄昏,外婆站在岭台上一声声叫着:“乖,乖娃,回家吃饭了”,声音悠远漫长。 外婆离去后的日子,我惧怕一个人的黑夜,惧怕一个人入睡的午后,惧怕夜是那样漫长,头疼失眠,夜夜不能入睡,半梦半醒之间,时时听到有人唤我,是二姨,是小姨,有时候是外婆,可醒来只有满屋子的清冷,外婆,我很想你,你是否能夜夜都来我的梦中...... (本期责任编辑:李向前/制作:薛伟)编委主任:赵克红 编委:朱欣英王小朋董进奎 王群芳吴文奇段新强 曲焕平余子愚张松焕 (以上为市作协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 总监审:赵克红(市作协主席) 主任、主编:吴文奇(市作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陈爱松杨亚丽李向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danhuaa.com/mdhxx/7188.html
- 上一篇文章: 种牡丹花品种图鉴大全,一睹为快
- 下一篇文章: 美哭了牡丹花开时,超全品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