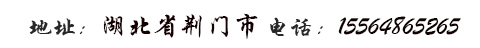长篇小说连载井石金梦劫第六回黑牡丹经
|
白颠疯图 http://pf.39.net/bdfyy/bdfrczy/180807/6442885.html 上回说到马元的队伍过日月山时,被警察局长的副官挡住,说要查他的砂娃队伍里有没有逃犯。马元心里一抽,这肯定是借名敲诈,心里想如何躲过此难时,突然发现副官面熟,便笑问:“这位兄弟我咋觉着见过面,你是?” “我是省局的。” 马元认出来了:“你是张副官!” 副官恍惚地看看马元:“你是……” “原来开皮货行的,马元。” “哦,对对对,马掌柜,失敬了失敬了,不好意思,兄弟我也是奉了局长之命,不得不来验查……如今不是非常时期嘛,又是逃兵又是贼,还有,”他放低了声,“我们局长又叫一个丫头片子戳了一刀,差点送了命哪!” 马元也低声地:“局长遇刺之事我知道,真是不幸,我给他那把藏刀,是想带给他吉祥,没想到那刀子差点要了局长的命,那丫头也太厉害了些。可你说那丫头在我的队伍里?”他觉着可笑,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真会开玩笑!金场里不能进女人,这是铁的规矩。女人进了金场,金山也要变沙山,我找女人进金场,不是自找倒霉吗?啊?哈哈哈哈……”他又笑。 副官也笑:“是啊是啊,你们挖金子的是讲究这些,其实啊,我们也不光是找那吃了豹子胆的野丫头,还有其他的逃犯。如今的人,犯了事十有八九往西口外跑,这你也知道。前两天过了一队砂娃,我们从那里面就查出了两个逃兵!奶奶的。” “对对对。请张副官放心,我雇的砂娃全是有名有姓有户口有根底的,”他又对刘拿事,“大家都不容易,这地方又冷,给兄弟们留下点酒钱。” “是。”刘拿事立即从兜里掏出一红包来,放在一警察手中。 马元说:“一点小意思,还望笑纳。要是我发了财出来,一定到府上拜谢。” 副官笑笑说:“马掌柜你这就客气了。”一挥手,“放行!” 警察们离开了岗位,砂娃队伍朝日月山的另一面走去。尕顺子、张八斤和贺永祥的脚步走得最快。 庄稼地一下子就没有了,撒落在草原上的,是点点的白色,那是牧人的羊群。新草还没出头,只有去年的席芨草高高地在风中摇曳。远处有一藏家汉子在唱“拉伊”,那平和委婉的声调和山的另一边农业区的“花儿”比起来,别是一番感觉。 马元顾不得这些,他让保镖管事们赶紧了砂娃队伍,披星戴月朝南昆仑、北祁连的八百里瀚海深处走去不提。 话说离马元要去的月亮河金场一山之隔的地方有一块凹地,叫野牛沟。从野牛沟呈放射状分出去好几条路,这些路都是砂娃们踏出来的,路的尽头都是金场。 因为野牛沟是去那些金场的必经之地,便有了一个由参差不齐的十来间极简易的土坯房组成的小市场。这是专门赶来做金场生意的季节性集市,有打铁钉马掌的,有卖杂货的,其中有一家的门上挂着“湟中实业有限公司”的牌子,就是官家为金掌柜们提供劳动工具及生活用品的机构。它的旁边是一家酒店,房头上立的杆子上挂帘一酒幌,上面写着“西来顺酒店”几个大字。 酒店旁边有口井,一个十六七岁的伙计在旧木轮车车轮做成的井架前打水,他叫尕六子。 店外,另一个叫来娃的伙计在肉架前帮一位有五十来岁的哑巴伙夫卸宰杀好的野牛肉。地上铺着刚剥下来的牛皮,一只硕大的野牛头骨挂在门的上方。 这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惟一的酒店的女老板是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外号黑牡丹。她泼辣大方,虽黑,但有专业妓女的韵味。原为妓女出身的她带了秀儿、湘儿、萍儿等三个姑娘来这里开店,将“西来顺酒家”弄成了妓院和酒店合二为一的产物,专门挣金掌柜们的钱。 给马元打前站的钱有主按定好的时间来这里等马元的队伍,掐指头算,马元他们上路早过了一个多月,这两天该到了。这会儿,闲得没事干的钱有主在给他的马刷毛。老板娘从店里出来。她抬头看看天,又看看前后,对钱有主说:“看样子,你们掌柜的今儿个还是来不了。” 来娃子抬头问:“干妈,你的意思是这肉先不煮了?” 老板娘骂:“放你妈妈的屁!不煮肉,客人来了吃啥?” “来不了好哇,我陪你多睡两晚上。”钱有主说。 “这话你给你妈说去。”老板娘故意板起脸说。 “哈哈哈哈!”来娃子大笑。 “你笑你妈妈的脚!”老板娘踢了来娃子一脚。 尕六子在井台上喊:“老板娘,这井绳快断了!” “你不会接好哇!你那狗爪子让野狐子吃掉啦?” 尕六子不言传了,他在井台上悄声发牢骚:“啥都让我干,我偏不接!”他把井绳一撂,提着桶走了。 突然,哑巴拽了一下女老板的衣襟,指着远处呜呜哇哇地喊。老板娘回头一看,只见远方一阵尘土飞起。 老板娘见状拍一下钱有主的肩:“哟,芝麻掉进针眼里了,看这巧劲儿,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钱有主没明白老板娘的话:“啥意思?” 黑牡丹眉飞色舞地说:“你家掌柜的们到了!尕六子,赶紧把火给我烧起来。来娃子,把肉全放进大锅里!”又搡了哑巴一下,做了个让他准备做饭的手势。 大家忙了起来。钱有主朝那远处飞起的尘土看了半天,不见人影,有点不相信女老板的话。然而,大概过了一个时辰,马元的队伍果然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又过了半个多时辰,马元和刘拿事他们骑着马先过来了。 钱有主跑过去抓住了马元的马:“哎呀掌柜的,我在这里等你们都等了整整两天了。” “路上不好走,我们晚到了一天。”马元看看四周,“这里蛮热闹嘛!” 尕六子和来娃子分别抓住马元及刘拿事他们的马往槽上拴。另外两个姑娘萍儿和湘儿也跑出来看热闹。钱有主指指姑娘对马元一挤眼:“还有更热闹的呐,这些姑娘都是冲着你们这些金掌柜们来的,这四周的山里有六七个金场。” 马元“哦”一声,指着一处山梁问:“那就是察汗大坂?” 钱有主摇头说:“不,那是俄包梁,翻过俄包梁还有两天的路是孟牛头他们的老窝扎曲滩,你往这面看,那像马鞍子的山梁才是我们要翻的察汗大坂。翻过大坂,再有多半天的路就到月亮河。” 马元看看西斜的太阳,问钱有主:“你的意思是今晚要在这里住一宿?” “那你的意思是要连夜赶路?” “我可是想现在就到月亮河!算啦,就好好住一夜吧,这一路走的,我可是把罪受够了。” 酒店的门帘一挑,老板娘黑牡丹急步走了出来,她走到马元走前,先笑稀了脸,说:“哟,这就是马掌柜呀!一脸的福相,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哪!” 马元问钱有主:“这位是?” 钱有主一指酒店幌子:“西来顺酒店女老板,黑牡丹。” 黑牡丹佯怒地:“去去去。” 马元由衷地赞叹:“好家伙,一个女人家,把店开到了西口外,你比孙二娘还厉害呀!” 女老板笑着说:“远天远地地到这里来,就指望马掌柜发大财呀!” 马元不理解地:“你,指望我发财?” “是啊,只要你们各路的金掌柜都发了大财,我这小店不就热火了吗?” 马元大笑:“噢?哈哈哈哈!” 女老板也笑着回头招呼那两个姑娘:“湘儿,滚茶!多放些荆芥姜片!萍儿,进去倒洗脸水!” 听到这喊声,马元的心情好极了。 陆陆续续地,砂娃们全赶到了野牛沟,他们东倒西歪地开始休息。小伙子们看见这里有姑娘,围过来稀奇地看。尕顺子也发现了她们,她不知道这些身上穿得如此光鲜的姑娘们在这里干什么,但她的心中突然就有了一种亲切感,真想过去和她们说说话,可一想到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早成了男娃娃,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叫财娃的砂娃拍拍尕顺子的肩说:“日奶奶了的,你看那个娘们的大奶头!等老子有了钱,得来好好睡她一次!”尕顺子的脸一下子红了,她马上明白了这些姑娘的身份,低下头,朝一边里走去。 酒店附近,清脆的叮当声有节奏地响着,这声响来自铁匠铺,那里面,一老一少两个人正在打铁。那柱子上挂满了新打出来的马掌。 刘拿事走到铁匠铺前,看看那些马掌,对那老铁匠说:“你是早知道我们要来呀。” 老铁匠停住手中的锤说:“我连你们有几头骡子几匹马都知道!” “我们可是明儿一早就要上路。” “上路前保证你的骡马个个挂上新掌!” “要是挂不完呢?” “那我就一个子儿也不要你的!” “好!像个闯西口的样子。” 老铁匠不高兴了:“小子哎,老子在这里盖这铁匠铺子时你还在你阿大的腿绊里转经呢,给我说这话!” 这一句话呛得刘拿事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摇摇头,去喊人赶骡子拉马了。老铁匠朝自己的掌心里吐了一口吐沫,又将那锤高高举起,铁匠铺里的叮当声又非常有节奏地响了起来。 “湟中实业公司”的门开了,一个叫秀儿的姑娘从那门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长衫的人,这人便是该公司驻这里的高老板。他看看西周,朝酒店走了过去。 马元正在洗脸,高老板过来了。高老板朝马元两拳相抱,问:“这位就是马掌柜了?” 马元:“您是……” 高老板一指他的牌子,用手抖抖他衣服上的土,说:“敝人姓高,湟中实业公司在这里的代理人,往后马掌柜的金场里缺啥,就从我这里提了用,账等出了金场再清。” “哦,好好好,”马元也抱了双拳说,“看来我们以后要打的交道不少啊!那就要请高掌柜多多帮忙了!” “这是敝人分内的事,理该如此,理该如此。” “高掌柜请进去喝茶。” “一起进一起进。” 大家这就相让着进了酒店。 走了几十天路的砂娃们累坏了,他们散坐在店前的地上,有几个人从井里打一桶水出来,好多人拥上去舀了喝。而更多的人却已经把被子朝地上一撂,躺在上面睡着了。 老板娘出来喊:“有钱的进来吃肉,没钱的把碗拿出来,每人一碗牛肉汤!” 尕六子和来娃子抬出一口锅来,往一个坑凹处安放好,里面全是牛肉汤。满仓他们拿了碗过去,来娃子就舀了汤给他们。 张八斤说:“老板娘,你是菩萨心肠啊。” 老板娘看一眼张八斤:“你们也别给老娘戴高帽儿,就这一次,一是看你们路上走了几十天的面子,二是让你们尝尝我的牛肉汤的味道。牛肉汤也是肉煮出来的,下回再来我的店,就得收钱,要不你们每次来,光喝肉汤不吃肉,我做屁的买卖。” 张八斤故意和她缠话:“要是我们挣不上钱,你连屁的买卖也做不成!” “这位哥,出门在外,可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贺永祥走过来,他把一口汤咽进肚子说:“老板娘,他这老鸹鸹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平日里打个嗝比放个屁还臭,你得多包涵。” 砂娃们笑了起来。贺永祥在和老板娘搭讪的同时,给张八斤一个眼色,女老板一走,贺永祥就跟了过去问:“老板娘,去拉萨做买卖的马队也是从这里过是吧?” “不走这条路,他们都得死!”她说着进了厨房。贺永祥朝厨房里看看,也跟了进去。 张八斤正在喝肉汤,贺永祥回来了。他看没有人注意,就嘴里喊:“变变变!”手从衣服底下出来,竟端着一碗牛肉。两人相视一笑,就地一坐,大吃起来。 西来顺酒店和城里的酒店的不同之处是,里面两边是两处土炕,炕上铺着青毡,炕的中间放一张长条形炕桌。两炕之间的空地间放着几张极简易的桌凳,最里面是进厨房的门。 马元、高掌柜及刘拿事、钱有主等五六人坐在其中的一处炕上。桌子上摆着一大盘肉,肉是大块的,上面斜插着好几把镶有彩色蜡贝、松耳石的五尺藏刀。他们正在割肉大吃。老板娘在让客,萍儿秀儿湘儿站在炕沿底下伺候茶酒。 高掌柜不吃肉,他喝一口茶,看看狼一样吃肉的马元说:“只要你们的金子出得好,我们才有发财的机会。” 马元的嘴里憋了一嘴肉,他一边嚼,一边说:“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发不发财的,你高掌柜的财发定了。哪个金掌柜敢不用你们公司进来的东西呀?您可是代表官方的呀!” 高掌柜:“发财也是公司发,我们这些跑腿的能有多少便宜可占?” 老板娘端起一大碗酒:“你们不要光说光吃不喝嘛!来,马掌柜,路上累了这么多天,今儿个到了我的店,就等于到了你的家,来,先喝了这一碗!” 马元为难地说:“一下子来一碗?太多了吧?” 老板娘说:“你是怕我用蒙汗药麻翻了你绑在剥皮凳上?你放心,我们野牛沟有的是野味儿,用不着杀人取肉。” 大家笑起来。 高掌柜对马元说:“她就是剥你的皮挖你的心,今儿也不是时候。” 马元问:“为啥?” 高掌柜说:“你还没发上大财嘛!” 马元笑道:“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喝下去,喝醉了凭你怎么处置,我都认了!”说着接过碗一饮而尽。 老板娘接过碗看看说:“这还差不多。” 马元擦一把嘴说:“进金场的人这么多,可够你老板娘忙活的了。” “开店的怕闲不怕忙,只要有掌柜的这句话,我就高兴。” 钱有主接过话去:“老这样忙,就怕你连尿尿的工夫都不得。” 老板娘眼睛一翻:“我没尿尿的工夫,你小子就没的喝了。” “噗——”刘拿事被这话笑得喷出一口水来。 顺姐子一个人在酒店边转悠。她实在没想到能在这千里之外没人烟的地方看见这么多的女人。不管她们是干什么的,也是女人,比像她这样一天钻在男人堆里好。她多想留在这里,哪怕给他们扫地烧火也成呐。她看见那个叫秀儿的姑娘从店里出来了,就大了胆子过去叫:“姐姐。” 秀儿回头见是个尕砂娃在喊她,便问:“干啥?” 顺姐子说:“你能不能给你的干妈说说,把我也留下来,我帮你们干活,干那些你们不愿意干的活。” 秀儿一撇嘴:“你是瓜子还是傻子?干妈能把金掌柜的砂娃留在这里吗?再说了,我们这里缺的是像我这样能伺候金掌柜的大姑娘,要你一个脬蛋娃干啥?你能陪了掌柜的们睡觉?” 顺姐一听此话,脸上一阵热,低头不敢再说啥了。 那天晚上,酒店外的空地上睡满了砂娃。顺姐儿也找一个背风的地方打开被子心思重重地睡了。殊不知,在一个砂坑内,有个人此时的心思比尕顺儿还重。 马长命弄了一堆牛粪火在烤。他用一根棍子动动牛粪火,斜靠在坑壁上,将手伸进怀里。伸进去的手停住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异样的表情。手从怀中抽出来,捏着一个绣得很精美的毛蓝布烟荷包。烟荷包的两面都用彩色的扣线绣了图案,一面是“鱼儿钻莲”,一面是“蓝雀儿探梅”,花边是环环相扣的葵子。无论选线、花样,都让人感觉到这个绣了烟荷包的人的一片苦心与真情。 捏着烟荷包的马长命的面部表情,就像是吃了沙子在屙碌碡,谁见了谁难受。不用压了指头算,马长命记得清清楚楚,他已经两年没见春花的面了。 春花不是他的女人,春花是刘占龙的老婆。 然而,五年前,春花是他们庄子里的姑娘,是马长命心尖尖上的一疙瘩活肉。 他永远忘不了他俩在一个月光融融的夜里发过的山盟海誓:红铜的手镯儿合龙口,当成个宝贝了放下;活着时一辈子不丢手,死了就一处儿葬下!青羊离不开青石山,黄羊离不开草山,若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冰滩上开一朵牡丹! 山盟海誓发过不到半年,刘占龙就像一堵高高的城墙,横在了他们中间。 春花的阿大做买卖亏了本,欠了别人一百五十个大洋,没了办法,要拿春花换。一百五十个大洋是个天文数字。马长命算条好汉,但钱压好汉气短,不要说一百五十个当当响的银元,一时半会儿的,他连一百五十个麻钱儿也凑不起来。 刘家人拿出来了,用红纸包成根硬棍棍儿,沉甸甸地放到春花阿大手中。 那年年底,冰滩上没开牡丹花,春花却被来娶亲的人用一辆蒙了红线单子的大板车拉跑了。听着春花在车里大放悲声哭天嚎地,马长命急了,搬起一块石头砸在自己的头上,结果,石头也没烂,而他的脑门上却开了一道口子。鲜血快活地从口子里钻出来,流在他脸上,流进他的脖子里。 春花过门后,很少来坐娘家。好不容易来一趟,那驴日的刘占龙就像猎狗一样跟在春花身后。春花见了他,也像见了陌生人一样,脸上毫无表情。气得马长命几次想用半截子砖头闷翻刘占龙,或用一把尖刀戳进他的下腹部,可他终于没有那样做。那样做的结果很简单,春花当寡妇,他被拉去砍头,他阿妈失去惟一的亲人。 马长命苦苦地熬了两年,几乎从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偏不偏,春花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没月亮的夜,他浇完地里的水,堵了水口,一个人摸黑往家走,走到家门口,就看见黑暗处一个人影儿躲在门口那棵老柳树下。 “谁?”他停了脚步问。 “我。”春花声音抖抖地说。 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就是隔上一万年,他也能听出来。他吃惊异常。 “你,咋来了?” “我,来看看你。” 春花说这话的时候,从嗓子深处发出了一声哽咽,她一头扎进马长命的怀抱里。马长命要拉着春花进门,反被春花拖他到了庄子东头的破庙里。关于春花到婆家两年中的一切,长命没有从春花嘴中问出个所以然来。她只是哭,抱了长命的腰哽哽咽咽,没完没了。哭完了,春花就解开衣扣脱下衣服铺在破庙里的草堆上,躺了下去。 “长命哥,你要是不嫌我让人沾了身子,就来吧……” 马长命无法控制自己了,他扑在了春花的身上。两个人的喘息声合在了一起。栖息在破庙中的野鸽子被他们惊了起来,拍打着翅膀飞进了夜空。 半年后,马长命和春花又一次幽会时,春花指着她那锅底儿一样鼓起的肚子说:“长命哥,你我这一辈子不能明媒正娶当夫妻,可老天爷有眼,没叫我们俩儿白好一场。你记得‘花儿’里咋说的?‘我俩好比是藏金莲,夏天里开,秋天里结下个籽儿’,你记着,不管这个孽障往后姓了啥,都是你的骨肉,……” 从那以后,春花再也没来过娘家。后来,他听说春花生了个男娃娃。他多想见见他的精血,可就是见不着。然而此时此刻,抢了他心上人的情敌,他想弄死的刘占龙却和他一样,成了马元的砂娃,就睡在离他不远的一个沙坑里。 马长命想,这小子家不是有钱吗?有钱的主儿咋也成了人家的砂娃?他们家发生了什么?春花呢?难道春花在家里受罪吗?马长命的心里一紧,他不由得朝刘占龙睡觉的地方看去。 月光照在刘占龙身上,刘占龙并没有睡,他裹着毡袄,定定地躺在砂坑沿上,两眼望着月光发呆,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马元被黑牡丹他们灌醉了,黑牡丹让秀儿和萍儿扶了马元去休息,她们便将马元扶到酒店后院的一个房间里。这房间和青海东部农家的房间一样,里面是一处土炕。炕上的被子已经铺好了,桌上点着白铁皮油灯。 马元往炕上一躺,说:“好啦,你们去吧,去吧……”秀儿和萍儿出去了。 路上三十多天没睡个好觉的马元一见热炕,就像吃奶的娃娃见了妈妈般亲。他几下子将自己扒了个精光光,钻进暖暖的被窝。就要吹灯时,门被打开,走进一个人来,马元忽一下坐起来变了脸色。要知这人是谁,我们下回再说。 ◆本篇所用井石先生照片均由六月荷花女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井石谢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danhuaa.com/mdhzp/7231.html
- 上一篇文章: 追忆红色岁月,牢记初心使命黑牡丹建设
- 下一篇文章: 牡丹花开正娇艳,带你探秘王城公园静谧开放